(一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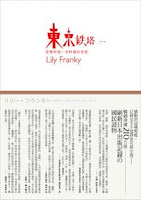
《東京鐵塔...老媽和我,有時還有老爸 》- Lily Franky
****
《東京鐵塔》是暢銷小說,又被拍成電視電影,多少是抱著「不能不讀」的羊群心理才看的。或許因為看了很多評論,早已大概知道故事內容,讀後是欠了一點點的感動。感覺就如在該哭的場合,想哭但擠不出眼淚時的納悶。
窮小子迷失於大都市,不顧家鄉孤獨的母親;到發現母親為他所作的犧牲時,卻逃不過生老病死的命運。Lily Franky 的真人真事,到底還是令人感動;而作者對老媽的愛,當然是不容置疑的。但小說好像太在意感不感人,有些文字彷彿在向讀者說「是應該哭的時候了」。反是那位「有時」才出場,口沒遮攔的窩囊老爸,更叫人好奇他究竟在想甚麼。他和妻兒分開三十多年,完全沒盡一丁點丈夫和父親責任;但老媽臨終時,卻讓人看到老爸是真的愛她的。
其實雅也和老媽的生活,平淡道來,已是很感人的如煙往事。最真的感情,是不須明言,讀者也能自我領會的。正如中譯本封面封底花團錦蔟的讚詞一樣(「足以讓二十一世紀的日本視為驕傲的作品」「一邊讀著,一個人無法自拔的淚流不止」「毫無疑問達成了現代日本文化的新里程碑」);由衷的讚美,經過這樣舖張的宣揚後,都無可避免地成了名過其實的虛譽。
我是頗喜歡這本小說的,只因為聽了太多好評,才覺得應該可以更好。我想《東京鐵塔》長長的故事,拍成賺人熱淚的電視連續劇,會比較合適。
(二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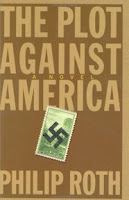
《The Plot against America》- Philip Roth
***1/2
《The Plot against America》是「虛構歷史」的小說:假如1940年羅斯福總統不能連任;假如華盛頓獨善其身,不加入二戰;美國國內的猶太人,會受到怎樣的對待?
雖然是虛構,但書中的政治角色,是真有其人的。故事主線是首位橫越大西洋的飛機師Charles Lindberg,憑反戰主張,擊敗羅斯福當選總統。 Lindberg總統姑息納粹的政策,令國內漫延起反猶太人的風潮。小說是一個住在新澤西州Newark的猶太男孩的回憶。他回憶一家人面對的困難,回憶1940至1942年動盪的歷史。
小說好看之處,是現實和虛擬交錯;加上納粹背後操縱美國政局的驚天陰謀,讓人看得十分緊張。雖然說的是二次大戰,我相信Roth亦是在暗裡比喻今天美國的政治生態。二戰結果黑白分明,誰是英雄,誰在賣國,讀者都一清二楚。但小說裡民主黨人極力主戰,被共和黨人斥為危言聳聽的情節,拿來對照今天兩黨的立場,亦頗耐人尋味。在錯綜複雜的政治糾纏中,要分出誰對誰錯,無論在1941年還是2002年,都不容易。
這麼好的概念,作者也做了詳盡的研究,可惜故事結構有點令人無所適從。小說開始時是比較緩慢的家庭片段,中段是緊湊的政治動盪,到結尾卻好像力不從心,不了了之。本來想給四顆半星的書,因為結局的敗筆,要扣掉一顆。
現實中的Lindberg,真的發表過反猶太人言論。小說提到的褔特車廠創辦人Henry Ford,更曾在旗下報章散播種族仇恨;希特勒甚至說過「我們視亨利福特為美國法西斯運動的領導人(We look to Heinrich Ford as the leader of the growing Fascist movement in America )」。原來在戰前的美國,納粹的反猶太主義是有市場的,並不只是三K黨等一小撮極端仇恨組織的偏見。
還是悲觀的一句:不過是六十年前的事。我們能不能相信,在這歷史眨一眨眼間,人類突然有了不讓悲劇重演的智慧?
(三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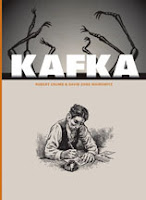
《Kafka 》- Robert Crumb & David Zane Mairowitz
*****
《Kafka》是一本漫畫,簡淺地介紹了卡夫卡的生平,他的創作動機,和他最著名的幾本作品。我差不多從來沒看過外國的漫畫書,只覺Crumb的畫風隱藏著一點兒超現實的神秘,很貼切卡夫卡的風格。(Crumb 是著名的漫畫家,記錄片《Crumb》,講述的便是他的創作經歷)。
Crumb的畫,和Mairowitz的文字,深入淺出地分釋卡夫卡內心和其作品間的聯繫。Mairowitz說,世人把卡夫卡變成了一個形容詞(Kafkaesque),卻看不到除了荒謬以外,他的故事幽默的一面。他小說中流露的壓抑,和對絶對權力的服從,源頭是來自他兇惡的父親,和在布拉格猶太貧民窟渡過的童年。但作者慨嘆道,在被忽略數十年後,今天卡夫卡已淪為布拉格招徠遊客的商業噱頭。
對卡夫卡所知很少,認識的只得《Metamorphosis》,《The Trial》,《The Castle》等故事古怪離奇的情節。《Kafka》薄薄一冊漫畫,個多小時便看完;對他認識深了,便再也不敢故作高深地把Kafkaesque這字隨便說出口。也是時候拿起書架上那兩本封了塵,買了十多年還未看完的《The Trial》和《The Castle》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